莆田安福家园 电影《唯一无二》爱与翱游

电影《唯一无二》改编自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叙述了一个听障家庭中唯一健听女孩喻延的成长故事。影片以家庭做事与个东说念主假想之间的矛盾为叙事中枢,致密地描摹了喻延在承担家庭重任与追求自我价值之间的贫瘠抉择与最终息争。它深刻地探究了家庭伦理对个体成长的真切影响,通过丰富的心绪细节,向不雅众传递削发庭与假想并非自然对立,而是在爱与贯穿中不错达成协调共识的理念。但是,在跨文化改编的进程中,影片虽尝试将原土家庭伦理不雅念融入其中,却在叙事结构和现本体感的呈现上出现了弱点,部分情节显得与试验脱节,悬浮于空中。如何让番邦电影文本在原土化语境中信得过落地生根,成为主创团队亟待贬责的关节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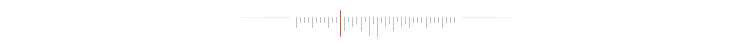
假想、家庭与自我认可
文|李旖琨
《唯一无二》改编自法国的《贝利叶一家》,同期也模仿了好意思国改编版《健听女孩》。影片深刻展现了假想与家庭这两大东说念主生焦虑命题,在关节手艺老是相互交汇、互为表里的复杂联系,以极简却充满张力的叙述作风,深刻揭示了家庭与个东说念主假想之间的矛盾及息争之说念。
影片叙述的故事配景修复于一个听障家庭的专有环境中。小男儿喻延手脚家庭中唯一健听者,自幼就承担起交流家东说念主与外界的做事。这种身份的绝顶性使她在成长的进程中形成了极强的做事感,却也因此牵累起千里重的热诚牵累与压力。
影片中屡次通过细节展示喻延承担着家庭与社会交流的“纽带”这一脚色,她不仅仅高中生、男儿,更是家庭中唯一与外界对话的出口,是总共家庭的“代言东说念主”。影片在宾客交涉、病院交流、银行业务、法庭解答这些细节中,都是在强化“纽带”这一脚色定位。导演毁灭了强力的戏剧冲突,通过特写镜头中的面部脸色、肢体抒发的描摹来具象化喻延的做事感。同期导演补充喻延的叔叔喻志成这一早期“家庭庄重者”形象,手脚“能听见”的第二条线,对照于喻延的窘境,他能听见是以“扯破”我方——这个脚色领有齐全的东说念主物弧光,千里默着给与做事,扯破我方的假想与心绪,早早耗尽我方贯穿与体谅的勇气,渴慕贯穿与爱。导演用拖沓诉说的方式来展示父亲分家产的“不公道”,叙述了一个铺张半生为家庭庄重的孩子,但愿用仅有一次的恣意获取一句公道的评价。

在家庭伦理建构的做事体系中,喻延承受着无声的压力,其个东说念见解志的醒觉促使她寻找突破的方式,音乐假想的萌生与成长,不仅是审好意思偏好的具象化抒发,更是主体突破家庭做事谈话拘谨、寻求自我认可的精神推行,以及达成寻找家庭做事与自我意志的焦虑前言。
影片对于喻延音乐假想的发展进程有致密的描写,除外婆的影响、齐唱的机会、淳厚的匡助等方式,向咱们展示芳华的迷惘与假想的选拔,更突显了处于芳华期的孩子对于期望和家庭选拔之间的内心热烈碰撞。
导演对于暖色调、柔柔的光影和即兴配乐的选拔,强化了音乐是喻延与天下之间的“无声”交流这一抒发。音乐对于她而言,是寻找自我认可与糊口价值的载体,同期亦然对抗试验生活的精神火器,是芳华成长的必经之路。影片往往使用无声的天下与音乐的天下产生强反差的方式强化冲突。追梦之路绝非一都坦途,拿下耳机,喻延回到试验生活,承担属于我方的做事。导演通过致密的神气,将母亲拽下耳机标识为对女孩假想的阻挡,他们以无声的“狡诈”方式将女孩拉下假想的列车,将芳华假想与家庭做事的冲突深刻化。

影片两次飞扬诀别发生在法庭吐露心声与喻延用音乐予以家东说念主“声息”的片断。第一次是幼年不得的爱与公道被“无声”宣之于口,是喻志成手脚第一代家庭发言东说念主半生的成长,达成了心绪与家庭的息争。第二次则是假想与爱的息争,家东说念主用骨传导“倾听”喻延的音乐与期望,逾越躯壳的笨重,走向爱。
导演私密地选拔骨传导的方式,使听障东说念主士突破躯壳的局限,更标识着交流方式的漂流,也用长镜头加特写的拍摄手法,将家东说念主第一次听到声息从慌乱到幸福浅笑的进程记载下来,感受到爱意在空气中流淌。此刻,喻延不再是家庭向外对话的纽带,音乐变成了他们共同感受的纽带。
影片好似迟缓流淌的溪流一般,将家庭息争的一刻简单地修复,喻志成归家的“喝一杯”和喻延追求假想时高铁上的黄色塑料袋展示了生活自己的形状,更焦虑的是,咱们看到家庭与假想并非对立面,而是在爱的津润下,会变成共识的部分。
(作家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商榷生)莆田安福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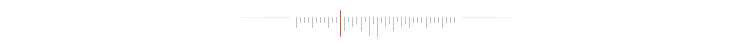
剥离于试验的改编
文|宋明海
电影《唯一无二》由王沐编剧并导演,作品改编自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与好意思国改编版块的《健听女孩》比拟,《唯一无二》同样连接了《贝利叶一家》中“听障家庭中健听女孩的成长窘境与音乐假想”这一主体成分,叙述了青娥喻延手脚听障家庭中唯一健听的家庭成员,不得不去濒临追寻音乐假想与督察家东说念主这一两难步地的故事。与前两部电影不同的是,《唯一无二》在叙事结构、影像作风和价值不雅念上均作念了要紧篡改,以期电影文本能在跨文化语境的改编中适配原土不雅众的审好意思教训与心绪需求。但在改编的进程中,电影暴泄漏“结构失力”“试验剥离”“转译偏差”的错误。
不论是原作《贝利叶一家》,已经改编版块《健听女孩》,二者都将作品的中枢冲突聚焦于家庭做事与个东说念主假想的扯破这少许,以健听个体与听障家庭之间自然存在的热诚隔膜与不雅念冲突,扩充降生份认可与成长困局等严肃议题,并对此进行深入挖掘。而《唯一无二》则选拔将中国式的家庭伦理不雅念融入电影文本之中,在电影叙事结构上作念了要紧鬈曲。

在叙事结构上,作品引入叔叔喻志成这一与喻延互为镜像联系的脚色,通过上一代东说念主的房产纠纷牵引削发庭牵记,并在法庭坚持中达故意绪认可与身份息争。这么的处理方式导致影片无数的篇幅被这条叙事痕迹占用,而主角喻延和哥哥喻周在十分的篇幅中只不错“失语”的景况参与情节推动,而非前两部作品中对健听个体与听障家庭成员之间心绪联系的深入挖掘。这么的修复导致了喻延的友情线、爱情线、师生线均被不同进程地压缩,在多重叙事痕迹并置下出现了东说念主物联系的“心绪裂痕”。其中,最直不雅的即是喻延的爱情线处理,这在前两部作品中均被深入挖掘,这是一条进展女主角热诚变化与成长历程的关节叙事痕迹,但在《唯一无二》中,爱情线男主角出现了大篇幅的“脚色失位”。不错说,这种剧作力量的散布,聚合体现为电影作品的“结构失力”。
原作《贝利叶一家》在影片中保留了在幽默中夹带调侃的圭臬笑剧作风,《健听女孩》则愈加贯注议题的严肃性与深刻性,尽管二者作风略有互异,但是都保留了视听的现本体感与情节的试验底色。反不雅《唯一无二》,后者在类型电影的交易逻辑与严肃抒发之间寻求均衡,却在量度与对冲中形成了电影的“局部失真”。

在电影质感的处理上,《唯一无二》过于依赖通过光影、色调与音乐来营造氛围进行煽情,这反而失去了归于本真背后的那份动东说念主力量。以三位女主角的团结次校园齐唱段落为例,前两部作品在处理这一桥段时,都致力收复或进展现场性的声息质感,克制音乐的煽情作用,在静默与歌声的交汇中以纯正和真情打动东说念主心。而《唯一无二》在处理这一桥段时,却变成一场极具煽情味的集体心绪宣泄。
在电影情节的处理上,影片开篇便以女主角的个东说念主独白完娶妻庭联系的先容,这种处理方式诚然能让不雅众快速赫然作品中的东说念主物联系,但是也因此丧失了细化东说念主物本性与东说念主物心绪联系的机会。这与前两部在具体的做事场景中层层渐进式的建构方式毫不相似。后续的法院坚持戏中同样存在此类问题,归结为少许,即是过于强调东说念主物的功能性,却丧失了东说念主物的试验底色,让故事剥离于试验之外,成为悬浮于试验之上的“空中楼阁”。
手脚一部跨文化改编的电影作品,如何让番邦电影文本在原土化语境中落地生根,是主创东说念主员在改编进程中亟需贬责的问题。电影《唯一无二》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不雅念重构电影文本,形成“家庭息争带给个体目田”的叙事战术,这一改编虽契合原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不雅念,但这种改编战术却对影片中的中枢议题“成长”带来宏大冲击。
传统家庭伦理不雅念在电影文本中的植入,还使影片在对于“听障群体”与“身份认可”的议题上出现“转译偏差”。举例,女主喻延的反抗仅停留在“时候被占用”的闹心上,而非深化到身份认可的迷濛与想考上,这与《贝利叶一家》和《健听女孩》在身份认可议题上的挖掘与反想形成对比。
电影《唯一无二》诚然存在部分改变错误,但不成否的是影片在跨文化改编中亦有可取之处,电影全体完成度很高,尤其是将原土传统家庭伦理不雅念与番邦电影文本进行交融的尝试,为后续的同类型作品集结了贵重的创作教训。
(作家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商榷生)